“群里的老師們,有認識這個蘑菇的嗎?我們這邊有幾個云南籍的務工人員在山上采食蘑菇后中毒了。”
5月底的一個求救信息,在“廣西毒蘑菇鑒定群”里炸開了鍋。中國疾控中心研究員李海蛟看到照片后立刻回復:“硬皮馬勃屬的,胃腸炎型毒蘑菇,有些伴有一定的神經毒性,不是劇毒的。”
就在大家松了口氣時,兩小時后群里另一張照片讓李海蛟瞬間警惕:“這是劇毒的灰花紋鵝膏!有幾人中毒?”
每年到這個時候,這樣的緊張時刻總會在全國十幾個“毒蘑菇群”里反復上演。作為食源性疾病中致死率最高的“殺手”,毒蘑菇的致命案例占比超過50%,而今年國內已有近10人因此喪命。
在李海蛟的實驗室里,來自全國各地的毒蘑菇樣本堆積如山。其中出鏡率最高的是大青褶傘,每年能 “承包” 1/4 到 1/3 的中毒事件。此外,劇毒鵝膏、近江粉褶蕈、日本紅菇、斑褶菇、牛肝菌等都是常見 “兇手”。
李海蛟曾參與國內2000余起蘑菇中毒事件的處置,每次得知中毒事件后,除了遠程為蘑菇識別和救治提供建議,他也會讓地方疾控中心將導致中毒的蘑菇樣品郵寄到中疾控位于北京的實驗室。“如果患者手頭有導致中毒的樣品,或者能給出采集位置,當地疾控會去采集樣品,烘干之后寄給我們,由我們做后續的鑒定工作。”李海蛟說。

致命鵝膏。
2024年,李海蛟參與了《中國毒蘑菇新修訂名錄》的發表工作,這項修訂工作由吉林農業大學教授圖力古爾主持,系統總結了我國大型真菌調查的成果,盤點、更新了我國的毒蘑菇狀況。
2025年,來自東北、華北、華中、華南、西南的五位真菌研究學者基于更新名錄,以及在實際救助指導中積累的豐富診治經驗,共同編著了《中國的毒蘑菇》一書。書中詳盡介紹了我國已知的毒蘑菇物種及中毒后的救治方法,滿足大眾科普需求的同時,也為疾控人員和醫護人員提供參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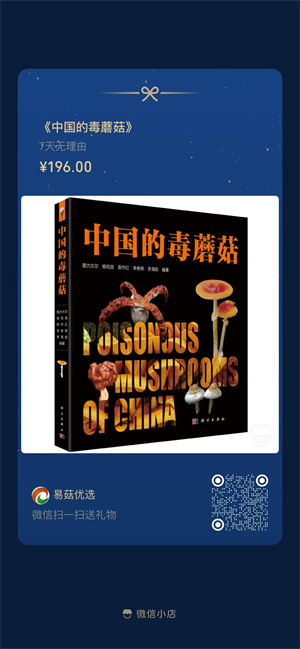
掃碼購買
然而,每年的蘑菇中毒事件仍然高發。以2024年為例,食源性疾病監測系統共報告了2800多起蘑菇中毒事件,涉及9000多人中毒,39人死亡。
在蘑菇中毒事件高發地區,采食蘑菇的行為仿佛刻在了當地人的基因里。“事實上,每年的蘑菇中毒案例,多數是山區百姓在采摘后誤食所致。”楊祝良強調。
還有一些自認為具備識別蘑菇經驗的人,他們中毒的比例同樣很高。“尤其是當科學知識與老百姓的傳統經驗發生沖突的時候,很多老百姓寧愿相信自己的經驗是對的。”李海蛟常說,不能盲目地相信所謂的經驗,這也是科普工作中的難點。
有的網友嘗試用人工智能(AI)識別、區分蘑菇,但李海蛟解釋,蘑菇大多為傘菌,由菌蓋和菌柄構成,可辨識的特征點極為有限,外觀又極為相似,不像植物有根、莖、葉、花、果,可辨識的特征很多。目前蘑菇物種的AI識別技術尚不成熟,國內也暫未開發相關的識別軟件。

可食的草雞樅鵝膏(左)和劇毒的灰花紋鵝膏(右)。

可食的稀褶紅菇(左)與劇毒的亞稀褶紅菇(右)。受訪者供圖
在李海蛟看來,毒蘑菇科普仍存在“最后一公里”的問題。那么,科普如何才能真正落實到那群采蘑菇的人?
如今各種專業的科普宣傳視頻、掛圖、廣播、條幅、游戲、講座等“轟炸式”手段,也在深入偏遠山區。比如,通過給山區中小學的孩子科普,孩子就可以告訴家里的大人,指出大人采蘑菇行為中的錯誤。“近些年,蘑菇中毒的死亡人數也出現了明顯的下降。”李海蛟說。
此外,李海蛟還強調關于蘑菇的生態科普。近年來,社交媒體上出現了一種“網紅”旅游項目——“撿菌團”活動。這種新式采蘑菇活動因“爆框”“打卡”“出片”被追捧,但背后是游客對蘑菇生長地的“掠奪式”掃蕩。網絡上頻頻有人指出,在這種破壞性采集之下,蘑菇都快被采光了。
李海蛟說,許多蘑菇是森林中的降解者,是森林物質和能量循環中不可或缺的部分,無序采集是對生物多樣性的破壞。“因此,我們強烈呼吁大家不要盲目到野外采蘑菇,建議以觀察、欣賞、學習為主。”













